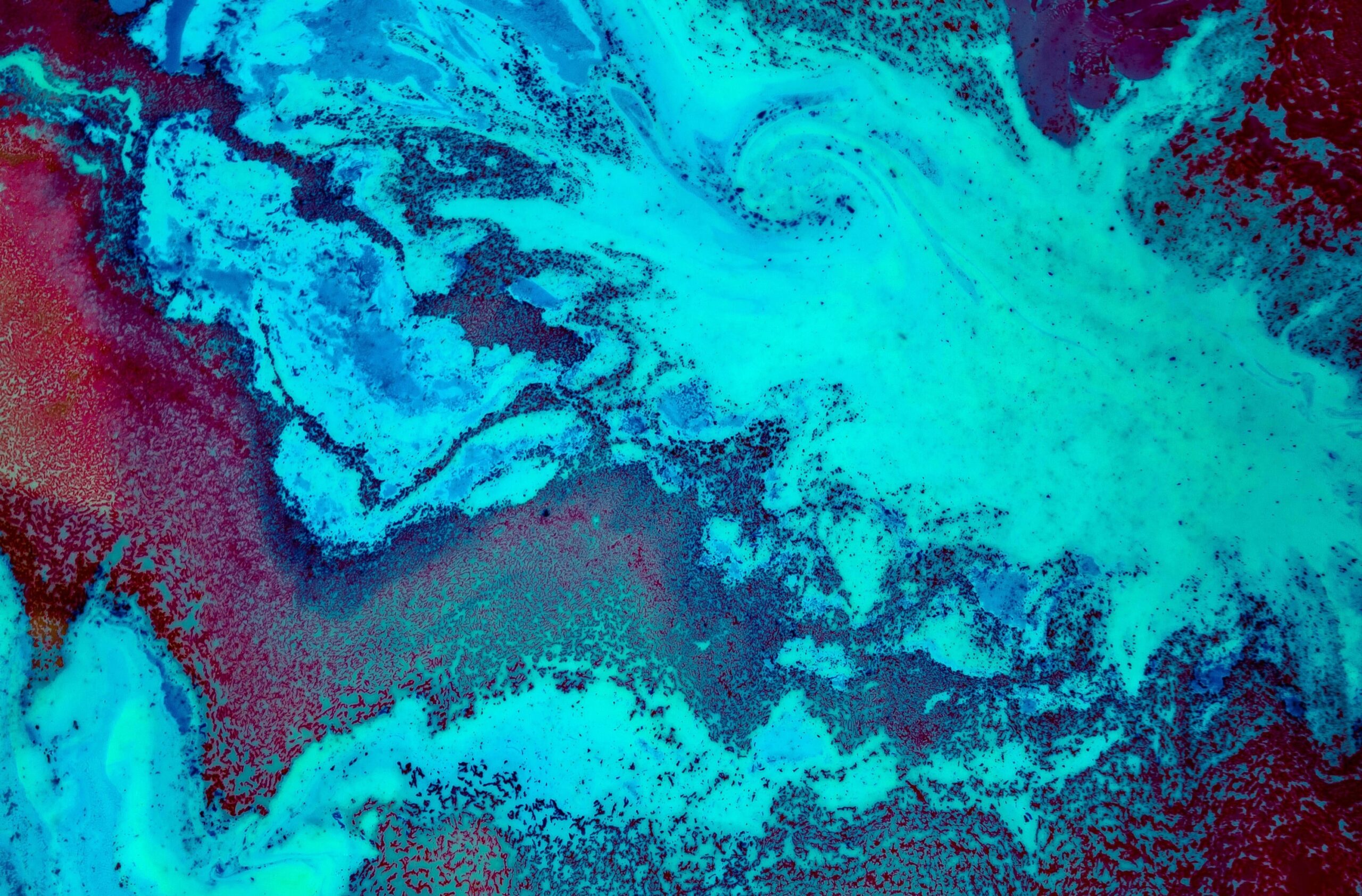你認同「週休三日」嗎?你認為週休三日能讓台灣社會更進步、更幸福嗎?在探討這個議題之前,不妨先回顧「休假」這件事是如何出現?又是怎麼一步步制度化的?
古時候的農業社會都是「週休零日」
在清朝以前,中國社會並沒有「星期」的概念,也就沒有固定的放假日。除了政府官員,大多數人是農民,作息隨自然節奏進行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農事活動與季節變化密切相關,雖然每日勞動,但沒有現代意義下的上班時間與工時規範。何時工作、何時休息,全憑生活需要與身體狀況調整,工作與休息的界線並不明確。
在沒有「一週七天」這種觀念之前,古代中國以農曆、節氣與干支系統來記日。一般人民的生活節奏多半依循「月初」「月中」「節氣」等自然或宗教時點進行調整,並非以週為單位來安排作息。農民依據農忙與農閒交替安排勞動與休息,官員則採行「五日一休」「十日一沐」等制度,由國家或地方行政管理層進行輪值與調班。部分地區也有「五日一市」的習慣,形成類似週期性的集市與休息節奏,但與現代「週末」或「星期日」的概念仍有本質差異。
因此,對於傳統社會而言,「休假」並非一種制度安排,而是依生活條件與農時自然出現的節奏。直到西方文化逐漸傳入東亞,來自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「星期日為休息日」觀念才被引介進中國。這種「七天一週、週日休息」的時間制度最早出現在通商口岸、教會學校與外籍醫院等西式體系中,對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是一種全新的作息安排。隨著報刊、學校與教堂推廣,「星期日不上班、不上課」的做法開始在少數都市地區出現,雖尚未制度化,但已為現代休假概念奠定了基礎。
1912 年,南京臨時政府宣布採用公曆為主、農曆為輔的曆制,正式將七日為一週的制度納入官方體系,這是中國首次從國家層級承認並施行「星期制」的現代時間結構。1929 年,國民政府頒布《國定假日例》,明文規定星期日為例假日,使週日休假首次具備法律依據與制度效力,也象徵「週日為休息日」這項概念從少數場域的實踐走向了全社會的制度化推行。
從政府與學校開始的「週休一日」
其實早在日治時期,台灣的小學(當時稱為公學校)就已採行每週六天上課、週日休息的制度,這與日本當時的學制同步,是台灣最早具備「週休一日」形式的教育作息安排。雖然這種制度主要出現在學校體系,對一般社會尚未構成廣泛影響,但也為戰後的週休觀念留下了基礎。
到了 1958 年,台灣政府正式推動現代化行政制度,開始在政府機關與公務員體系實施週休一日,通常為星期日,這被稱為「例假日制度」的開端。這項政策旨在與國際接軌、提升行政效率,也象徵台灣在體制上邁向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向。
隨後,學校系統也逐步配合政府作息進行調整。自 1960 年代起,國小與國中率先實施週日不上課,高中也陸續比照辦理。至於教會學校與外籍教育機構,則更早即採用類似的週日休假制度,在制度尚未普及前已扮演先行者角色。
真正使勞工休假權利進入法律保障的,是 1984 年《勞動基準法》的頒布,並於 1985 年正式實施。該法首次明文規定,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一日休息,稱為例假。不過,在制度初期,適用對象僅限於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與工廠,服務業與中小企業多未涵蓋在內,因此實際落實仍有明顯落差。
回顧台灣週休制度的歷程可以發現,從早期的民間先行、自發實踐,到政府制度化推動,再到教育體系與勞動法規的逐步接軌,學校在制度轉型中曾經扮演起始的角色,也顯示出在工時與休假制度的變革中,教育領域確實有可能成為率先試行的場域,並帶動整體社會逐步跟進。
依舊由學校打頭陣的「週休二日」
週休二日的推動,依然是從學校開始。早在 1990 年代初期,當時政府機關與多數企業仍維持週休一日,而部分國中小與高中已率先試辦「隔週休二日」,也就是一週上課六天、下一週上課五天的作息安排。在教育部鼓勵學校彈性排課的政策下,週六的課程逐漸轉為課外活動、社團或彈性課程,正式課程的比重也隨之淡化。
當時台灣的雙薪家庭尚未普遍,不少家庭仍由祖父母協助照顧孫子女,也常由年長子女照顧弟妹,因此學生週六放假對家庭而言影響不大,社會整體的接受度也相對穩定。
1998 年元旦起,政府機關率先實施隔週週休二日,作為政策轉型的試點,學校則全面配合調整作息。部分民間企業也開始參照政府作息,彈性安排週六是否上班,但當時尚未有法令明文規定。直到 2001 年,政府宣布全面實施週休二日,行政機關統一休六、日,國中小與高中也同步調整課表。勞基法亦在同年修法,將工時由「雙週 84 小時」改為「單週 40 小時」,週休二日正式成為全國普遍適用的勞動制度。雖然法律並未明文強制週六、日為假日,但在實務上,週休二日已全面落實。
從早期沒有固定休假日,到週休一日,再到週休二日,可以觀察到台灣休假制度的演變過程中,學校始終是最早實施變革的場域,行政體系與勞動制度則隨之配套調整,逐步推展至整體社會。
實施「週休三日」是好?還是壞?
從台灣過去週休制度的演變來看,學校經常扮演率先試行的角色。若未來朝向週休三日發展,學校極有可能再次成為第一個啟動的場域,例如先從隔週休週五的方式試行,逐步觀察成效與調整方向。
這樣的變革勢必會帶來各方面的影響。
從課業與學習層面來看,學生若多出一天假日,可安排更多非制式學習活動,像是閱讀、創作、社區服務或專題探索,有助於培養自主學習能力,也能減緩課業壓力。如果制度設計得當,週五可納入遠距學習或 STEAM 課程。然而,若沒有配套調整課程結構與升學制度,主科時數壓縮可能使教師與學生面臨更大負擔,高中生也可能因升學壓力將週五投入補習,產生「假日變成補課日」的副作用。
在家庭與家長面向,問題會更現實。多數家長仍維持五天工時,孩子週五放假,卻無法請假照顧,容易產生「照顧真空」。對低齡學童家庭而言,可能需要額外聘請托育或送安親班,形成經濟負擔。單親或雙薪家庭更容易受到影響。
不過,學校制度的改變,也有可能成為企業制度創新的催化劑。如果家長逐漸偏好選擇提供彈性工時或週五遠距工作的企業,那麼企業也會被迫轉型,導入更具家庭友善的工作制度。另一方面,社區與公共資源也有可能跟著活化,例如圖書館、博物館、社區中心提供週五學習活動,讓學生與家庭參與更多元的課外共學,減少對補習與安親的依賴,支持一個以社區為核心的學習與照顧網絡。
工時越長,真的代表越進步嗎?
目前台灣人一年平均工作約 250 天,相較之下,日本約為 200 天,德國則僅約 170 天。顯然,工時越長,並不等於生產力越高,也未必代表社會更進步。
我們往往以為古人生活辛苦、全年無休,彷彿沒有休假的概念。但事實卻恰好相反: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傳統社會,古人的實際工作天數,很可能比今天的現代人還要少。
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勞動節奏隨節氣運行,農忙時期雖需全力投入,農閒時卻能修繕器具、備料祭祖,甚至長時間休息。再加上春節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等固定節日,一年真正密集勞動的日數,大致落在 180 到 220 天之間。
古代官員與文人也並非全年執勤,除了常見的五日一休、旬休等制度,年終還能請假返鄉,來回動輒數十日。歐洲中世紀的農民也因宗教節日與主日禁工,每年可休息多達 150 至 180 天,生活節奏緩慢,禮拜、慶典與社交活動佔據了大量時間。
相比之下,現代工作者雖然擁有科技與制度保障,卻也更被工時綁住。不僅工作日更多,還時常在非上班時間回應訊息、持續待命,甚至週末也難以真正休息。工時雖可量化,但心理疲勞卻難以衡量,長期下來,反而讓人愈發難以感受到生活的餘裕。
或許,我們該重新思考:擁有週休二日的我們,是否才是那群真正沒有「好好休假」的人?
那麼,「週休三日」會是台灣下一場重要的社會制度變革嗎?從制度演進來看,我們確實已具備邁向週休三日的社會條件。只要配套完善、制度彈性,這不只是可能的選項,更是現代人找回生活節奏與喘息空間的一步關鍵。
我支持週休三日,因為這不只是勞動制度的調整,更是我們對「更好的生活」的集體想像與實踐。
Photo by Aziz Acharki on Unsplash
探索更多來自 吳致緯|管理顧問的觀點筆記 的內容
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