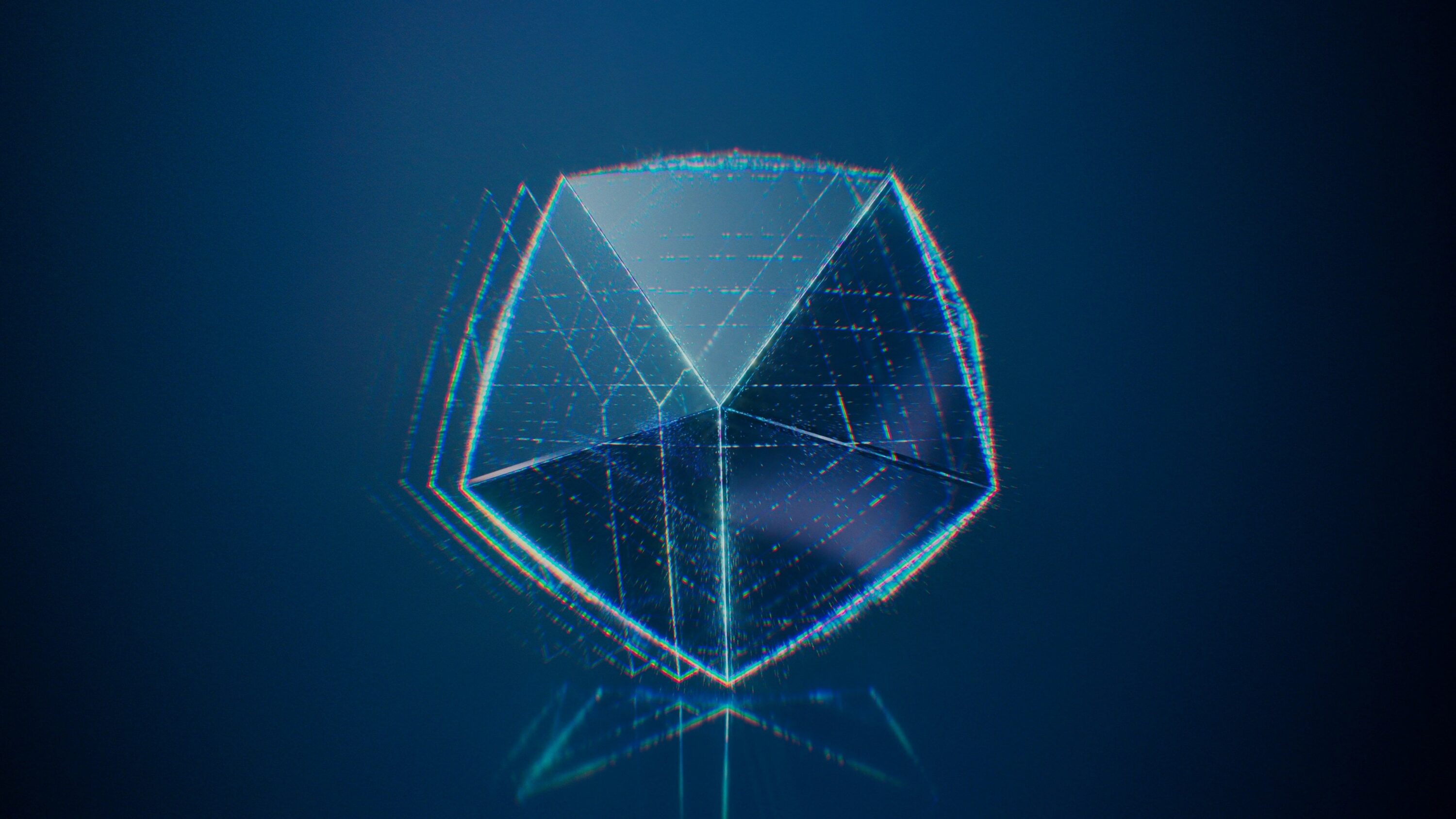你有沒有想過,如果全人類都不喝酒,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?
麥肯錫的研究指出,Z 世代正在嘗試減少酒精攝取,對於 Z 世代族群來說健康問題是更重要的。
沒有酒精我們可能會少掉很多麻煩。沒有宿醉、沒有酒駕事故、沒有酒後家暴與失控的社交局面。醫院裡因為肝硬化來求診的患者大量變少,婚宴上大家改喝果汁敬酒,便利商店的冰櫃也不再有那些罐裝啤酒佔據一整排貨架。世界變得清醒,似乎也更乾淨了。但歷史上,這個看似理想的狀態,其實曾經真實發生過。
1920 年,美國正式啟動了全國性的禁酒令,也就是《憲法第十八修正案》的實施。當時的美國社會充滿理想主義與宗教道德運動的聲浪,許多基督教團體與女性禁酒組織將酗酒視為導致家庭破碎、社會墮落的元兇。他們認為,只要把酒從人們的生活中移除,社會問題便能迎刃而解。
禁酒令的通過與執行,被視為一場「道德淨化運動」。它禁止製造、運輸與販賣任何酒精含量超過 0.5% 的飲品,理論上全國將進入一個沒有酒精的時代。但法律並未禁止「飲用」本身,因此只要有人能取得酒,喝是合法的——這為未來的漏洞埋下了伏筆。在禁酒令剛開始的幾個月內,確實有統計數字顯示酒類銷量下降、公共秩序改善、工人遲到與工傷率下降。許多支持者以為理想國度即將實現。但不久後,社會就開始出現極大的裂痕。
由於合法酒精供應全面中斷,整個國家的飲酒活動迅速轉入地下。私釀酒、走私酒、偽裝醫療用途的藥酒成為黑市熱賣商品。美國各大城市出現成千上萬間秘密酒吧(Speakeasy),有的藏在理髮廳、有的在劇院地下室,人們透過暗號或推薦才能進入。當時的紐約市光是非法酒吧就超過兩萬家,比禁酒前還多。這個黑市經濟極快地吸引了組織犯罪的介入,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芝加哥的黑幫首領艾爾·卡彭(Al Capone)。他靠販酒致富,掌握警察與政客,甚至經營慈善形象來洗白。毒販、幫派火拼、警局收賄、司法癱瘓… 禁酒令不但沒有讓社會變得更清潔,反而催生出一個酒精驅動的地下世界,治安更差、暴力更頻。
另一方面,政府也面臨稅收大幅下滑的問題。在此之前,酒類稅是聯邦政府的一大收入來源。禁酒後這筆錢消失了,但打擊走私與維持執法的成本卻大幅上升,使得公共財政更為緊張。尤其進入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之後,民眾對政府施政的信心開始動搖,禁酒令成為眾矢之的。終於在 1933 年,美國國會通過《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》,正式廢除禁酒令,結束了這場長達十三年的國家實驗。這也是美國憲政史上唯一一次,一條憲法修正案被另一條修正案所推翻。
回顧這段歷史,禁酒令的本意其實並不邪惡,它來自於一種對社會秩序與家庭安定的期望。但這個案例清楚地告訴我們:當一項政策忽視人性、無視需求,單靠禁止來達成目標時,它最終只會讓問題轉入更複雜、更隱密的狀態中發展。其實這不只是酒的問題,而是「限制」本身的問題。當我們企圖透過法律、制度或規定來全面壓制某種行為時,若沒有搭配理解、溝通與替代方案,結果往往不會是矯正,而是轉移。人類會繞過去,會另尋出路,甚至會用更激烈的方式去完成那個「被禁止」的動作,因為禁令本身就成了一種誘惑。
這樣的現象,其實我們日常生活裡也常常看得到。有些家長從小禁止孩子打電動,覺得那是浪費時間、不務正業,於是用壓力、監控、規定把孩子推離螢幕。乍看之下孩子好像變得很乖,但等到他考上大學、搬出去住的那一刻,補償心理便像洪水一樣潰堤。有人一玩就是十小時起跳,有人甚至因此頻繁翹課,而錯過該探索自我、建立目標的黃金階段。
父母口中的「控制」並沒有變成教育,反而延後了問題的爆發。學校也常出現類似的限制。像是有些嚴格禁止學生談戀愛的校規,本意也許是希望學生專心課業,但卻忽略了情感探索本就是青春期重要的一部分。結果學生只好在校規陰影下偷偷交往、學會隱瞞、說謊,甚至用更激烈的方式去表達情緒與依附。戀愛本身不是問題,但當它變成違禁品,反而可能產生壓抑、扭曲,甚至創傷。
在職場裡也有相同的狀況。有些公司對上下班時間抓得非常緊,每天打卡遲到一分鐘就扣薪,強調紀律、制度與規範。但這樣的限制卻往往造成另一種文化:員工學會了「裝忙」,時間不等於產出,待在辦公室不等於真正有在工作。看起來秩序井然,實則效率低落,因為限制只是讓人變得會演,不是真正激發責任感。
言論空間亦是如此。當某些社群平台開始封鎖、審查敏感言論時,那些聲音不是消失了,而是轉向更匿名、更極端的論壇或暗網發酵。你看不到,不代表它不存在。過度限制的結果不是平靜,而是潛流暗湧。
甚至連飲食也一樣。當一個人對自己設下過度嚴格的節食規則——絕對不能吃甜的、炸的、澱粉——也許短期內看起來「很有毅力」,但現實中很多人會陷入另一種迴圈:壓抑→暴食→內疚→再壓抑。不是每個人都適合靠意志力長期壓制慾望,沒有空間、沒有彈性的限制,最終只會摧毀自我關係。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例子是性教育。
在某些文化保守的社會中,性被視為禁忌,不但不教避孕,也不談身體界線,甚至連正確的身體知識都被當成危險資訊處理。結果是青少年反而在無知與好奇之下做出更高風險的選擇,發生性病感染、意外懷孕的機率更高。限制知識,從來不等於保護,反而可能導致更深的傷害。
人類為什麼會這樣?因為我們在面對壓力、焦慮、不確定感的時候,會本能地尋找出口。而這些出口如果被堵住,壓力就會轉向別的地方發洩。酒精,其實也只是出口之一。有人靠它放鬆,有人用它逃避,有人把它當社交的潤滑劑、創作的靈感泉源。當我們談論「如果全人類都不喝酒」,我們其實在問的是: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出口,我們會怎麼辦?
也許我們會轉向無酒精飲品、CBD(大麻二酚)、冥想、極限運動或虛擬世界的沉浸式逃避。也許會發明新的成癮物質,也許會創造新的社交儀式來取代「乾杯」這個動作。但說到底,這不會是「更清醒」的世界,只是「用別的方式繼續微醺」的人類而已。
這些現象,不只是個人或社會的問題,其實也深刻反映在企業管理當中。許多公司制度中的「限制」原意是為了維持秩序或提升效率,但若設計過度僵化、缺乏信任與理解,反而會削弱整體組織的活力。有些企業限制員工在工作中不能滑手機、不能聽音樂、不能遠端工作,企圖以高度控制換取工作專注。但這些表面規範如果沒有與工作內容、產業性質對應思考,最後可能只會流失創意人才、讓主管花更多時間盯人,整體組織的信任基礎反而被一點一滴地削弱。
限制制度如果沒有搭配清楚的「目標導向」、「自我管理機制」與「結果負責文化」,就會從治理工具變成創意與行動的天花板。尤其是面對 Z 世代與高自主性工作者,越來越多人才追求的不只是薪水與穩定,而是「我能不能在這裡有空間、有選擇、有成長」。這些價值觀與過去傳統企業的「控制思維」若不調整,最終留下的可能不是效率高的人,而是習慣順從的人。
回過頭來看,如果我們從「不喝酒」這個假設延伸出的,是對人類如何尋找出口、如何被限制所形塑的反思,那麼對企業經營者來說,也應該問問自己:我們的制度,是為了協助人專注與成長,還是只是讓他不會犯錯?我們的限制,是為了對齊目標,還是只是減少變數?
制度的存在,本該是為了支撐人的能動性,而不是取代它。好的限制應該創造方向與秩序,但如果缺乏對人性的理解與信任,那些制度終將成為企業無法成長的邊界。
當我們討論「如果人類不再需要用酒精逃避生活」,其實也可以套用到組織中——如果一間企業能減少讓人想逃的理由,那麼員工就不需要靠制度鬆綁或假裝服從來尋找空間。真正的組織健康,不在於限制得多嚴,而在於限制是否讓每個人都更接近共同的目標。
探索更多來自 吳致緯|管理顧問的觀點筆記 的內容
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。